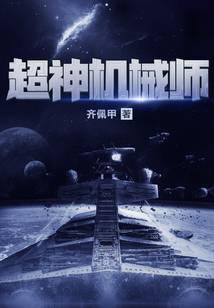川北地區的秋天,高陽依舊聚熱,早晨的殘霜已經化成了水霧,這些水霧凝聚了又飛散,變成了這兒那兒的雲朵,像一塊塊抹帕似的把天空洗的湛藍藍的。
大地更亮了,早晨間還是蒙黃的一片,瞬間成了金黃的河山。
鄉下人早上出發,黃昏回來,一天的秋忙在年青人的口哨中就是一首快歌。
小路上的葉子們被人們踩得稀巴粉碎,這就是萬物成泥的定理。
它們不能比擬星空,日月,不比白天和黑夜。
淺薄的生命隻有一次,如同人類一樣,終極化作泥土,就是這個道理。
農活再忙也有人不忙,他們有萬多的理由不去田地,林小端就是其中一個。
她剛從醫院回來,身體還沒有完全複原,還穿著一件病號衣。
這不奇怪,她的思想是再也不想給這個家出力了,這件衣服證明她還是個病人,像這樣的人什麽活也乾不了。
不要人專門伺候,已經算不錯了,這就是她不去勞動的理由。
身上這兒那兒的傷痕,挨的輕的,它們已經愈合了,即使這樣也可以看見逐漸在消失的痕跡;挨的較重的,正在愈合,即使愈合了也消不出那種痕跡。
“這就是證據!
”她常在心裡怒吼。
她在醫院的時間隻有兩天,蘇傳林隻給了她兩天的治療時間。
第二天天色剛黑就和他爸往回擡,把她丟在床上,生怕有人知道了去告發他這個暴徒。
此外,麥子高粱已經熟透了,分不出一個人來去醫院照顧她這個閑人。
放在家裡少花錢,還能做個飯。
他給他爸說這是皮外傷,不是絕症。
她有點小聰明,蘇傳林在家時就悶在鋪頭睡。
前腳剛走又掙紮著爬了起來,這種堅強也是為了一個人。
她身上疼痛,但如果看見那個人,那種疼痛就會莫名其妙的減輕和消失,轉成一種舒服感。
那天他抱她,已經感觸到了這個男人的力量,是差了一些,還不夠壯實。
可那種肌膚的細膩和火熱的胸膛讓人心饞,永遠巴在心頭想。
他的一切都看見過,她想,她就是他初次的女人。
每每想到了這種程度就會害羞的偷著笑,禁不住還要擡起頭來偷望還不算很遠的背影。
看他那副忙碌樣,還真想跑去幫他,一輩子也不離開。
蘇童爸的病一直沒有好轉,因為家裡沒錢,又加上秋忙,一直拖病在床上。
原來,在幾天以前隻咳嗽,昨天和今天偶爾吐血。
地裡和田裡的活隻能靠蘇童毛毛躁躁的亂忙一通。
他媽一直在家侯著他爸落氣,好埋了後抽身去幫娃,不然得把娃累死。
她娘家哥哥,就是那個老光棍來過一次,前天來的,一看這人不行了,昨天又走了。
留下了僅有的一百元錢,忙著回去秋收,走時說忙完了就過來擡屍。
蘇童也出去借過很多次錢,因人太年輕,嘴上沒毛,先前借的沒有還,再借已更難了。
那位老來的赤腳醫生倒是看上了那件風衣,願意出個半價,蘇童暫時沒有答應,也沒有拒絕,在考慮中。
救父親的命他比誰都急,即使那件風衣賣出去了也管不了事,連醫院的門檻也進不了。
那是楊慧林贈送的,是她跑幾百路專門給他買的,如果賣出去了,往後怎麽面對?他沒有穿不等於不喜歡,這種場合是鄉下,而又正農忙。
大熱的天穿件時髦的風衣出去秋收,這就是一個十足顯擺的瘋子,誰還不知道他的家底呢?
他一面割著麥子一面流著眼淚,急的哇哇叫。
自己還是個男子漢,已經這麽高的人了,眼睜睜看著父親落氣,卻束手無策,窩囊廢。
“我就是個窩囊廢……”這話已經在麥地裡嚷了很多次,像頭牛一樣在地裡頭跑來跑去的割。
麥粒乾蹦了,落下的比他收的多。
蘇童所做的一切,那種焦急,那種吼叫和出去借錢的事,都一一被林小端看在眼裡了。
她沒有錢卻有值錢的貨,我們以前說過蘇傳林跑她逃跑,一直困著,幾乎沒有給她拿過什麽錢,用的東西都是蘇傳林買回來。
但是別忘了,在雲南老家,那時候蘇傳林為了討人家的歡心,買了兩件首飾,項鏈和戒指。
到了蘇家,因經常挨揍,那值錢的東西也不方便戴身了。
裝在盒子裡,藏在一個紅漆箱子的下面。
蘇傳林曾看見過兩次,後來再也沒去理了。
現在看見蘇童急成那樣,她決定要拿出了,讓蘇童去縣城賣了救他爸。
如果還不夠,乾脆,把自己也賣了。
如其死在蘇傳林家不如把自己賣幾個錢,或許還能救活他爸。
當時她是那樣想的,而且認為一點也不荒誕。
白白跟蘇傳林這個暴徒同床睡覺,不如給喜歡的人賣春救父。
反正她要破罐子破摔了,即使去做娼也不跟他過下去了。
可是,在時間上是不允許的,按照蘇城卿目前的病狀,怕是等不到她付出去做娼的那個地步。
看見蘇童背著一筐麥穗回來,還光著膀子把她瞄了一眼,林小端心花怒放的轉身進了屋。
蘇童已經知道她回來了。
夜裡根本沒心思睡覺,他爸的咳嗽聲也讓人睡不了,和他媽換著時間經管父親,生怕突然過去了。
窗戶正對著蘇傳林的家,看到那兩爺子擡著林小端進的門。
“怎麽回來了?”他當時也嘀咕了一句。
林小端現在不敢跟蘇童接觸,要把那些東西送出去很困難。
項鏈和戒指已經拿了出來,雖然值錢她卻覺得可惡,正是這些東西讓人輕浮上當。
當初說什麽代表永恆,代表愛,全是些哄人的鬼話。
現在要把這些惡心的玩意統統處理,重新做人。
她終於還是邁出去了,那種緊張的氣氛連空氣也跟著凝聚了。
若是看見或逮住了,就不是住院那麽簡單,搞不好把命也送了出去,那個暴徒的尖刀真是讓人無比驚恐。
她想把那些東西丟下就走,如果有話說,最多一兩句。
“童童!
”她喊了一聲。
蘇童剛一擡頭,眼前一個女人就把一種涼冰冰的東西已塞進了手中。
他的視線當時是模糊的,那個女人來的快,差點與他身貼著臉。
這種距離確實一時難辨,讓人不止後退一步。
林小端還看見了他赤裸的胳膊上有好多麥穗劃出來的血印,這一幕讓她回去心疼的咒罵蘇傳林。
“把它們賣了救你爸!
”
蘇童才剛把人看清楚又馬上要跑,是堂嫂,居然跑來的這個女人是堂嫂。
曾經被揍的奄奄一息的,傷痕累累的女人。
連一句說話的機會都沒有給他,眼見那背影正拐了過去時蘇童像是已看見了她的心。
蘇童目瞪口呆了,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,她的善良會害了她自己,蘇傳林發起瘋來會打死人的,一種驚駭認識到這東西不能要。
他正要還回去時看見蘇傳林回來了,正在他們家的屋背後。
“先保管起來再說吧!
”他自言自語地一頭紮進了屋裡。
“剛才屋外嚷嚷是誰?”她媽問,正往外走,母子倆一進一出。
“一個問路的。
”蘇童說,“媽,爸怎麽樣了?”
他媽搖了搖頭,說:“看樣子已經不行了,我去找你舅舅,讓他過來幫著收拾。
”
他媽的表情十分悲痛,即使在孩子面前也堅強不了裝出來的剛硬。
前段時間還勸娃放開些,真正到了這一天,那種裝出來的剛硬猛地垮塌了。
男人走了,這個家庭不是缺一個人的事那麽簡單。
很多種原因混合在一起,譬如少了勞動力,那份土地會被集體收回去。
家裡沒了頂梁柱,重活路丟給一個不滿二十的孩子;那麽多帳哪個還得起,孩子沒有父親,連娶媳婦的事也不好保證了,楊明清的大女子恐怕再也不會來了。
母親走了,蘇童看著這個家庭,除了一口鍋和兩把鋤頭,它們還能當碎鐵賣以外,沒有一件是值錢的了。
那件時髦風衣是楊慧林送的,手裡的黃金首飾是林小端送的,如果處理它們就會簽下合同似的人情。
他來到他爸的臥室裡,房間裡盡管收拾的乾淨,但仍舊有一股刺鼻的腥味。
盆子裡那些因溫度而凝成團的血塊被草木灰掩蓋著,父親一動不動的仰著身子躺在床上。
氣息微弱,在寂靜無聲的房間裡隻有無力的咳嗽聲。
當時的那副樣子是很嚇人的。
因連日不能進食,瘦的隻剩下一副空皮囊了。
眼睛成空洞似的從面孔上也凹了進去,嘴唇上沒有一絲血色,像抹了一層冷灰。
“爸!
”他喊了一聲。
蘇城卿知道自己不行了,快要死的人大多數都知道要走的大期,時間也就在這一兩天了。
聽見娃在喊他,像英雄似的振作起來也失敗了。
沒有了力氣,沒有了精神,老是咳死人。
丟人,恨自己拖垮了家庭。
他有心裡話,讓母子倆不要管他,讓兒子趁早把糧食收回來。
有飯吃才有往後的日子!
可是,蘇城卿說不出來了,那雙空洞的眼睛把兒子看了一眼,嘴皮子動了一下就昏過去了。
蘇童抱住他爸,鬧了半天,這才醒了過來。
這種情況時有發生,但昨天和今天與前段時間相比,昏厥的次數又增加了一次。
風衣和黃金首飾就在身旁,這兩件值錢貨經讓蘇童動心了,在典當或則是賣出去之前,他必須要去一個地方。
那是一個新的希望,是突然間從腦海裡跳出來的希望。
以前沒想過,是把所有的地方想遍了才跳了出來。
他小時候看見有些窮人去找那座房子裡頭的人,並在那兒領到了救濟,包括糧食和錢。
現在那些窮人有的還活著,房子裡的人也換了一批。
他如法炮製,去敲那座房子的門。
那兩扇門原本是敞開著的,也一直對外敞開著。
中午陣陽光的暴曬,才不得不暫時性虛掩著。
裡面的人說:“進來!
”
蘇童走了進去,一個中年男人接待了他。
“有什麽事我們可以幫到你?”那人說。
“我爸病了,快要死了。
家裡能換成錢的隻有一口鍋和兩把鋤頭,我不得已又不忍心才來找到你們。
”
“你說吧!
”那人說。
“我想跟大隊借錢。
”
蘇童是光著膀子去的,從麥地裡回來連件衣服也顧上穿。
像他這樣不穿上衣的的年青人在鄉下到處都是。
那人猶豫了一下,起身跟他說:“你等一下。
”
這是一間寬敞的屋子,整座房子是經原來的保管室改造的。
現在成了大隊辦公室,所謂的改造隻不過是搬了一些凳子和幾張桌子,而後在門楣上掛了一個醒目的牌子。
那個人進了左邊的一間小屋,很快就出來了。
跟他一起出來的是一個面容顯瘦的人,大約五十出頭。
“你剛才說的事情我們已經知道了。
”那人說,“大隊上一時拿不出那麽多錢來,你看這樣行不行,我們想辦法湊湊,在天黑之前一定派人去你的家裡。
”
蘇童回去了,他們說的很認真,像是一顆定心丸。
無論怎麽樣?這是唯一的希望了!
正如他們說的那樣,在天黑之前那兩個人來了。
從一個黑色的皮夾子裡拿出了一打票子,蘇童也沒數,像長了飛毛腿一樣,背起他爸就往縣醫院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