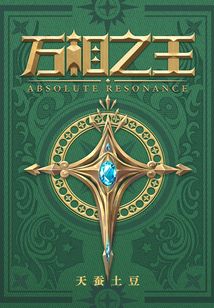(上章已替換成正文內容,大家重新下載一遍應該就能看到了)(今天這章依舊沒寫完,先放一些亂七八糟的稿子,新書開頭之類的)
(電腦今天去找人修了,那人說沒救了/嚴重懷疑是物業草台班子,技術不行)
(花了一上午時間把所有軟件下載回來,然後從郵箱、WPS、各個寫作軟件的備份中還原了部份稿子)
(損失依舊慘重,最慘的是我那好幾個G的學習資料沒了)
(從今天開始戒色)
“我叫張成文,從事互聯網方面的工作,半年前剛從公司辭職,現在主要做一些外包。
“我和死者是鄰居,和死者的父親是在登山途中遇到的,算是忘年交吧。
說起來,我在死者家附近買房,也是因為死者父親的緣故。
“當時我辭職來到江城,人生地不熟的,每天也就爬爬山。
那次在登山途中遇到了死者父親,感覺挺聊得來的,就將房子買在了他們家旁邊,互相也好有個照應。
“我和死者的關系……哈哈,死者父親知道我單身,想撮合我和她在一起,但我討厭她那樣的人,又不想壞了兩家關系,就沒有直接拒絕,隻是冷處理。
“偶爾,死者父親會邀請我去他們家吃飯,飯後會打幾輪牌,要是晚了我就住在他們家。
他們家的鑰匙也給了我一份,缺什麽東西可以去拿,他們衣服要是忘收了,我看到也好去幫忙收掉。
“今天早上死者父母都上班去了,忽然就下起了大雨,我想去幫他們收衣服,一進門就看見死者吊在客廳的吊燈上,舌頭從嘴巴裡吐到了下巴上,腳懸在下面晃來蕩去,屎尿流了一地,真是狼狽醜陋啊……
“我將她放了下來,就打電話報警了。
對了,我早年間混過社會,膽子練得比較大,所以不怎麽害怕。
他們也都說我這人沒心沒肺,待人冷漠,可能確實如此吧。
”
“我和死者有沒有更親密的關系?
沒有,這個肯定不會有的,她是那種很典型的‘小仙女’,我很討厭這類女的,連看一眼都嫌惡心。
”
“為什麽辭職?
因為工作壓力太大了啊,哈哈,你也知道做我們這行的,大部分都是禿頂。
”
“為什麽來江城?
有朋友在這兒嘛,來見見朋友,順便參加一下他的葬禮,哈哈。
”
……
錄像至此結束,畫面中的中年男人西裝革履,花白的頭髮整齊地梳在腦後,露出略高的發際線,一派IT行業精英的模樣。
陳述信息時的態度卻冷靜得不似常人,最後甚至還流露出幾分死豬不怕開水燙的嬉皮笑臉。
“白棋,你怎麽看這個案子?
”徐子秦輕拖鼠標,將進度條拉回中間,點下暫停。
他一身棕色外套,亂糟糟的頭髮下是同樣歪七扭八的衣裝,光站在那兒,沒人能想到他是江城治安局的刑警隊長。
“張成文身上嫌疑最大,但沒有任何證據留下,局裡那邊已經將他放了,可我總覺得心裡不踏實。
”徐子秦斜靠在電腦桌側,腳跟一點一點的,“你聽他這幾句話說的,不是明擺著在挑釁嗎?
”
白棋坐在輪椅上,拿著幾張案發現場的照片翻看了一會兒,道:“聽口供,張成文和死者一家不熟,至少情感上有很大的隔閡。
“他厭惡甚至憎恨死者,對死者的死亡感到快意,如果不是心理變態,那麽大概率曾經和死者有什麽過節。
”
“我也這麽覺得。
”徐子秦讚同地點頭,“但他說他天生冷漠,一緊張就喜歡狂笑,這死無對證的,我能怎麽辦?
”
“你要是意外死亡,我說口供時肯定會直呼你的名字,哪怕想笑也會出於人道主義忍一會兒。
”白棋將照片放到腿上,盯著自己的手看,“連名字都不肯出口,隻以‘死者’二字代稱,簡直是生分到了極點。
”
“你這話……但還是沒證據啊。
”
“所以,你是想讓我幫你偽造證據嗎?
”白棋擡眼,似笑非笑地看著徐子秦。
徐子秦怎舌:“這玩笑可不興開啊!
我這不是想,當年在警校你刑偵和勘察都是第一,說不定能看出點東西來嘛。
”
白棋不語,從一堆照片中挑出一張死者屍體的正面像。
一身紅色長裙的長發女子平躺在地,年輕的臉蒼白如紙,舌頭從紫色的嘴唇中伸出半截,脖頸下嵌著一道猙獰的勒痕。
“法醫應該已經排除其他死亡方式,確定是縊吊死了吧?
我記得,縊吊死很容易區分是自殺還是他殺。
“自殺者隻會有一道勒痕位於下頜與脖頸相接處,且腳尖自然下垂;由他人勒死再懸掛上去的屍體會有兩道勒痕,一道位於脖頸,一道位於下頜。
“從照片看,死者是自殺無疑。
我很好奇,你為什麽執意認為這是一起刑事案件?
”
白棋不等徐子秦回話,又拿起一張夾竹桃花的特寫,放在屍體照片的正上方。
“我或許可以試著理解你。
在驗屍的過程中,法醫在屍體的喉管中發現了這朵夾竹桃花,並檢測到了張成文的指紋,確定這朵花是他在死者死後放進去的。
“但恕我直言,有罪推定最要不得,張成文的行為充其量構成侮辱屍體罪,和謀殺死者一事並無直接關系。
“畢竟,現有證據已經足夠證明死者是自殺的了。
”
徐子秦沉默兩秒,搖了搖頭:“但我還是覺得不對勁。
好好一小姑娘,聽鄰居說性格一直挺開朗樂觀的,平日裡也就在家打打遊戲,和誰都沒有矛盾,怎麽說自殺就自殺了?
”
這些信息是寫在檔案裡的。
死者名叫盧語琴,二十四歲,大學畢業後待業在家,被父母呵護得很好,無心理疾病,無自殺征兆,誰能想得到她會在一個雨中的清晨上吊?
沉默在公寓中蔓延,良久,白棋低聲念道:“清晨陰氣未散,陽氣甫生,正是陰陽交替,人鬼衝撞之時。
外頭又下雨,陰氣從地下隨雨水蒸騰入人間,人倘若在這段時間運勢低迷,很容易被鬼遮了眼,攝了性命。
”
他的聲音陰惻惻的,徐子秦聽得一愣,轉而一拍他的肩:“老戚,你成天在家裡宅著發黴,怎還迷信上了?
咱信奉唯物主義,不談牛鬼蛇神。
”
白棋不置可否地笑笑,說:“行,那我們說回這個案子吧。
“我可以提供一個思路:夾竹桃的花語是‘謾罵’,張成文在口供中不止一次提到自己從事互聯網相關工作,你或許可以從死者的瀏覽記錄查起,找出自殺或者謀殺的動機。
“因為遭受謾罵而自殺,因為謾罵他人而被謀殺,都是不錯的故事,不是麽?
”
“照你這麽說,張成文還是故意留下線索,好讓我們去查他的?
”徐子秦皺起眉頭,腳跟重重地砸在地闆上。
“誰說不是呢?
”白棋拔下電腦上的U盤,和照片、檔案一並放進文件袋,塞回徐子秦懷中,“你要是真想查他,我再給你一個建議吧——
“弄明白他在江城的朋友是誰。
”
……
徐子秦走後,白棋搖著輪椅進入洗手間,在特別設計的低矮洗手台前停住。
鏡中映出一張蒼白而清秀的屬於年輕人的臉,眼角的猩紅血絲如有生命般遊動,幾乎要奪眶而出。
白棋靜靜地注視著鏡中的自己一會兒,伸手擰開水龍頭,接了點水潑到臉上。
冰涼的無形之物肆意流淌,格外能使人冷靜;眼中的血絲漸次褪去,恢復如墨的烏黑。
白棋緩慢地轉向,控制電子輪椅向陽台的方向移動。
一路上房門都沒有關,他長驅直入,將輪椅停在陽台的玻璃門邊。
陽台中的躺椅上,一個紅衣女子的虛影略顯局促地坐著。
她濃密的長發從額前垂下,瀑布似的遮去半張臉龐;拉長的舌頭從發間吐出,像是霸王花噴吐的花蕊,格外引人注目。
——正是照片中上吊自殺的死者。
白棋看著女人,在唇角勾出一抹微笑:“盧語琴,現在我們來談談你的事吧。
“比如——你死時的感受?
”
……
白棋喜歡了解死者的故事,那會讓他感到快樂。
因為對於正常人來說,沒有什麽是比死亡更為痛苦的事兒了。
而幸福等感受是要通過對比才能得出的。
就像搖著輪椅的人沿街慢行,過往的路人向其投去同情的目光,其中不乏夾雜幾分屬於手腳健全者的確幸,慶幸自己在某一領域的條件比下有餘。
咂摸他人的痛苦,才能知道自己此刻的處境尚有變遭的餘地,未雨綢繆也好,幸災樂禍也罷,總比沉浸在自己的悲慘人生中自怨自艾要幸福。
白棋喜歡咀嚼痛苦,包括旁人的和自己的,並且不憚於手動製造一些慘劇。
這是一種變態心理,作為反社會人格障礙的一種,促成了數以萬計的連環殺人案,並在上個世紀光榮地成為了臭名昭著的前額葉切除手術的研究課題。
白棋系統性地學過心理學,能夠客觀地診斷出自己的病症。
但他並不覺得這有什麽不好,畢竟現代人或多或少都有點心理問題。
超過九成人自認為自己存在心理疾病,更有四成人已經通過各種渠道確診,他作為病友大軍中的一員,並沒有什麽出奇。
鑒於法律的存在和偵查體系的完善,白棋很好地克制住了自己的衝動,二十六年來從未親手殺過一個人。
並且他通過殺死雞鴨貓狗等動物的嘗試,確定了:簡單的血腥殺戮並不能帶給他快感。
他所癡迷的,是富有美感和藝術性的謀殺,是高智商罪犯表演式的完美犯罪,和哥德巴赫猜想亦或者莎士比亞戲劇沒什麽本質區別。
他沉迷於刑偵小說,尤其是真實事件改編的,有具體案件細節的那些,並總是對那些罪犯的疏忽嗤之以鼻。
後來,他以高考714分的高分報考了警校刑偵專業,不出所料被錄取,並以優異的成績畢業,被分配到南城治安局刑偵大隊工作。
明面上,他讓所有人相信他有一腔懲惡揚善的正義感;暗地裡,他如饑似渴地翻閱刑事案件的卷宗,為那些血腥悲慘的故事著迷。
短短四年,他接連破獲了兩百多起刑事案件,聲名鵲起。
可惜好景不長,在一起惡劣的連環殺人案中,他受了重傷,包括生理上和心理上的。
結果就是,哪怕身體在康復後,各個組件都沒有毛病,他卻不知為何再也站不起來了,隻能坐在輪椅上度日。
他也因此從一線退了下來,在幕後做刑警大隊的顧問,負責幫忙看看卷宗,提提建議。
這在旁人看來是天妒英才,他卻甘之如飴。
畢竟,簡單地破獲案件已經不能帶給他快感了,每每看到那些粗糙劣質的作案手法他都惡心欲嘔。
他在期待一場完美犯罪,而退居幕後的日子讓他有足夠的閑心制定犯罪計劃。
在今年年初,老同學徐子秦被調到了江城,他也跟著搬了過來,繼續從事顧問的工作。
那些尚未來得及試試的犯罪計劃,和他一起來到江城。
……
大周西南道,雲州清徐縣。
餘暉已沉,夜色漸深,嫋嫋白霧繚繞,啾啾烏鵲歸巢。
城外竹林間,顏彧和一位老和尚、一個少年圍石而坐。
青色巨石上,穩穩當當地擺放著一個酒壇和三個破碗瓢。
穿舊袈裟的老和尚端起破瓢,給自己灌了一口酒,對顏彧道:“後生,老朽同你說,那長安也沒什麽好的,不良人夜夜就捉咱們這些沒門路的妖怪呐。
”
他佝僂著脊背,撚須而歎:“若是被抓著了,運氣好的當幾個月苦力,運氣差的,可是要被拿去給女皇煉丹的。
”
旁邊的少年捧著酒碗啄飲,聞言擡頭幫腔:“我飛進宮看過那女皇洗澡,五十出頭的人還白嫩得跟個豆蔻少女似的,不知吃了多少我同族的精魄!
”
一老一少兩個妖怪一齊看向坐在青石上的顏彧,露出森森的白牙:“你且說,是不是這個道理?
”
顏彧十六七歲的少年模樣,著藍布長衫,一根藍頭巾束發,臉白得像鬼,被山林間浮動的綠火襯得幽幽。
他拱了拱手,喟然道:“晚輩不得不去長安。
家父在晚輩十歲那年離家,為不良人所害,埋骨於長安;家慈三月前也去往長安,路途中遇上開倉放糧,數目不對,他們硬說是妖怪動的手腳……”
少年唾罵:“那些人類最不是東西,尤其是不良人!
”
老和尚也道:“成日裡找我們麻煩,還冠上些莫須有的罪名,我們劫他們的糧做甚?
簡直是無稽之談!
”(本章完)